*本文原载天津日报(2021年06月15日)第09版“人物”,文:张艺桐
原文网址:http://epaper.tianjinwe.com/tjrb/html/2021-06/15/content_159_4598099.htm

刘擎,著名学者,华东师范大学教授,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、西方思想史、现当代西方思潮与国际政治问题。代表著作《纷争的年代》《悬而未决的时刻》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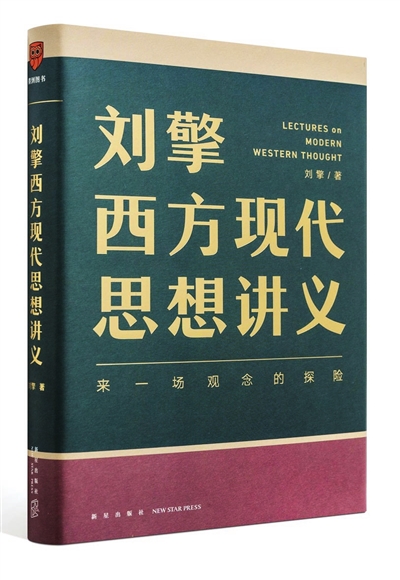
印象:哲学家“出圈”,“宝藏导师”上线
刘擎58岁,相貌温厚,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了将近20年的书,专注于一个对大众来说有些冷门的专业──政治哲学,他是典型的“学院派”,身上有着和专业气质相符的沉静和睿智。
从书斋里的学者到网上的“宝藏导师”,刘擎在猝不及防地“出圈”之后,日子突然忙碌起来。比如最近他就先后去了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成都、重庆等城市,举办新书《2000年以来的西方》《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分享会。现场人气甚旺,“粉丝”甚至爆发出欢呼尖叫声。刘擎说:“这场面感觉很不真实。还好我已不年轻,不然很可能被冲昏头脑。”
专业学者走出书斋成为明星的案例并不陌生,十多年前,易中天、梁小民、王立群、阎崇年、钱文忠等专家、教授通过电视平台成为社会名人,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。近两三年,互联网促生了“网红教授”,刘擎便是其中之一,他与年轻人的互动黏度更高,分享的课题也更加生活化。比如在《奇葩说》中,他与经济学教授薛兆丰以“学哲学和经济学,哪个更有助于找对象”为题的辩论,刘擎总能以大众能够接受的角度,有力地、准确地传达出一些不特别晦涩但有一定深度,明显看出哲学思考方式的观点。这或许跟他文理科兼修的知识背景和文艺青年的经历有关。
上世纪80年代初,刘擎毕业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,两年半后获该校该系工学硕士。虽然学业顺利,但他更迷恋文艺,创办戏剧社参与演出,他写于1985年的诗作《四月的纪念》后来被乔榛、丁建华朗诵。他决定转行,上世纪90年代初,刘擎赴美留学,攻读政治学获博士学位。2003年回国在华东师大任教,自此开始每年撰写《西方思想年度述评》,是许多学者每年必读的文章,哲学家陈嘉映称“国内没有第二人可以写出来”。
在《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一书中,他选取了韦伯、尼采、弗洛伊德等19位知名学者,通俗易懂地讲解了这些思想家的成就,探讨了他们关注的问题。“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,帮助大家去理解、反思我们的现代生活。”这也是刘擎在“得到APP”上讲课的内容。
引导大众读者阅读哲学,哪怕只有一点收获也好
记者:很多人看到您在辩论节目上的言论,被深深吸引并且爱上了哲学,想要去学哲学。您觉得大众这种对思考的兴趣会比较长久地延续下去吗?还是说,只是暂时看看热闹?
刘擎:我还真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。我目前的感受是,大部分人只是觉得我的说法比较新鲜而已。我最近出的书,比如《西方现代思想讲义》《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》,或者其他一些书,起到的是一个桥梁作用,引导非专业人士去阅读更深刻的哲学书。到底有多少人会顺着这条路走下去,我完全不知道,但是我觉得,哪怕一些人只是看个热闹,也没关系,有一点收获,总比完全没有要好。
记者:作为哲学教授,写面向非专业大众读者的作品,是知识降维吗?
刘擎:不能这么说。生活是复杂的,情感的结构是复杂的。我并不觉得我比别人多一个维度。我希望我的书是一种思考的邀请,大家一起来探讨。没有谁一定是谁的导师,大家都是同学,最多我可以算得上学长。也不是我启蒙谁,是大家一起思考。
记者:现在各种辩论、脱口秀节目很火。很多辩论就仅仅是为了辩论而辩论,就是为了压倒对方,为了赢得辩论,而不是双方为了抵达一个真理,您怎么看?
刘擎:像我参加《奇葩说》,也是要争输赢,但双方还是充分展开了各自的观点,而且还有一个第三方,可以有机会去支持一个你原本并不认同的观点。
记者: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知识普及度的提高,但现在过度追求点击率或者流量,以至于流量成了指挥棒,甚至有人产生了“流量焦虑”,如果自己发布的内容没有流量,好像就被世界抛弃了。作为严肃的学者,您怎么看这种心态?
刘擎:我想这种状况的背后,是单一的评价思维。我们小时候的单一评价标准是“学习成绩”,长大了就是“赚钱成功”。如今网络上流量成为唯一的标准,要改变这种单一评价标准的状况,需要有流量的人来告诉大家,“流量不是唯一重要的。”至于焦虑,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。只要有人的存在,有对比,有评价,就几乎一定会有焦虑。我希望我们不要被单一的评价标准所囚禁,让那些没有流量,在评价标准中比较弱势的人,也有生存的空间。
记者:您每年都会做西方思想年度述评,非常受欢迎,被知识界广为称道,是思想界的一道年度大餐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,对此您有怎样的感受和思考?
刘擎:我当然也一直没有停止对疫情的观察、思考、感受,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者看法。这个世界不是线性的,它变好,不是一条直线,变坏,也不是。历史和时代总是起起伏伏的。虽然深刻的思想者往往都是悲观的,但我还是选择做一个乐观主义者,因为我个人认同这样一个理念──人首先要相信事情会变好,它往往才会有变好的可能性。
思考是一种生活方式,并不是哲学家的特权
记者:比如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的作品,被全世界的大学教授或者一流的作家读到,吸收营养后,再去以自己的方式转化和阐释,然后被大众接受。那么现在您作为哲学教授,通过大众媒介直接对网友讲哲学,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?
刘擎:我认为这个意义有很多个方面。比如说,普通人的生活也是需要哲学思考的。这不光是为了体现一种人文关怀。还有就是,“哲学问题”不应该有太多的专业术语,不应该与大众隔开。从原初的状态来说,苏格拉底、柏拉图一开始就是在生活中谈哲学,哲学的最初驱动力来自日常生活。只是后来,学术分科,哲学才变得更精深和专业化。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生活中,回到哲学的原初面貌。试图对当下这种既焦虑又奋进,既高兴又沮丧等等复杂的生活感受进行辨析,是我从事哲学思考的原动力。另外一方面,对于大众来说,思考本身也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,并不是哲学家的特权。这种思考,不是说一定要获得多大的学术成就。苏格拉底说,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,其实,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过着哲学生活。只是要提高这种自觉性。
记者:现在有些年轻人通过看短视频学习知识,您觉得这种方式与通过文字阅读学习,差别到底在哪里?
刘擎:人接受影像主要是一种感知,跟人的直觉有关。而文字主要是文化、理智的产物。人阅读文字获得信息,需要进行主动的思想转化。现代文明很大程度是跟理智的成果相关。看短视频当然也可以学习知识,但是如果过度陷入短视频,可能就没办法把握现代文明中比较根基性的东西。作为消费端,看短视频获得信息就够了,但如果你要当一个创作者,光看视频肯定是不够的,还是要多读文字。
记者:但现实中很多人可能不具备思考能力,甚至逻辑混乱,出现交流障碍,影响到自己的工作。
刘擎:改善逻辑混乱的思维状况,正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所进行工作的价值所在。我不能说我可以起到多大的改变,但是我至少是一滴水,一粒沙,聚沙成塔,滴水穿石。不单是学者,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,一起来提高我们日常对话、思维的品质,汇聚成一种高质量的公共知识、精神生活。
一碗普通的鸡汤,也能喝出哲学的深度
记者:“内卷”是一个学术专业词汇,现在成了网络热词,您作何评价?
刘擎:一个学术词汇的走红,一定是因为这个词戳中了大众的某根神经,精准、简明地抓住了大家普遍感受到的一种状态,“内卷”这个词就是这样。我们的确在生活中见到过,不同行业存在一种高度竞争,但其实很多都是无效的,彼此抵消,无助于生产力的提高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,就会心领神会。
记者:对于想做点什么,又不想被内卷压垮的年轻人,您想跟他们分享怎样的心得、建议?
刘擎:对个人来说,某种程度的“卷”是不可避免的,但要尽量避免卷入过深,更不能沉湎其中。稍微卷一卷,这就是“微卷”策略。同时,也可以想办法卷出各种花样,所谓“花卷”。“花”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变成创新,说不定就走出了内卷。
记者:从最早的《读者》杂志,到微博再到抖音,心灵鸡汤从没缺席,您如何看待这种“浅思考”?
刘擎:我并不反对鸡汤,但不要止于鸡汤。鸡汤可以带来某种智慧的闪光,但是浮光掠影。如果你能从鸡汤中引发更深刻的思考,就是好的。比如我曾看到一句话说,“听遍了世界上所有道理,依然过不好这一生”,哇,这不是在说我吗!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深入追问、思考,为什么会这样?答案是,因为这些道理你只是听了,并没有真正弄懂,所以你过得不好。也就是说,哪怕是一碗普通的鸡汤,依然可以喝出深度,喝出原材料,喝出饲养场,喝出森林。
记者:年轻人容易为情所苦,以您的阅历与思想,现在如何看待爱情?
刘擎:我认为爱情就是要舍得自己,对方的幸福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。没有舍己为人,没有从算计中超脱,就没有爱情。法国哲学家阿兰·巴迪欧说,经典意义上的爱是一场小型的共产主义。当然,有的人在一段关系中,要的是经济安全或者其他东西。那也是一种选择。只不过,这样你就不要再问爱情的滋味是什么了。
记者:走入大众视野之后,接下来您在上节目参与思考分享和在高校做研究教学之间,如何平衡时间和精力?
刘擎:坦白说,我没有具体的计划,大概是根据自己的心性来参与。我自己当下的感受是,现在参加的节目太多了,深度、系统阅读的时间会受影响,这会让我感到不安,阅读已经是我本能的需求。如果哪天没有读书,我会觉得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。我想如果我再年轻20岁,或许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共空间的知识分享事业当中去。因为做一个面向大众发声的知识分子,往往比在学院里做教授影响力更大。但是,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已经让我形成了一个定势──我需要有足够安静的阅读时间。事实上,我把希望寄托于比我年轻的学者,我相信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,哪一天我这种“前浪”被拍在沙滩上,我会高兴的。
刘擎的年轻时代:读书激发了他的文艺天分
刘擎的父母是上海人,在上世纪50年代奔赴青海支援边疆建设。刘擎出生在青海,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,当时有一句名言,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,科学技术日新月异,而文科却一直在研究千百年前的老问题。1978年,15岁的刘擎考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(东华大学),读高分子化学专业。
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关心社会应该何去何从、人是什么、人性是什么,也许思想体系方面还比较粗糙、不够精致,但人们都有远大的理想抱负。尽管物质匮乏,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──社会生活、公共生活高于私人生活,都觉得津津乐道于私人生活是庸俗的体现。
有一次,一位国外的历史学教授来做讲座,从近代历史一直讲到现代社会,教授对人类的反思深深触动了刘擎的内心,为他打开了一扇人文社科领域的大门。他开始大量阅读,他读完了四卷本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罗曼·罗兰成为他心中的英雄。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也是在那个阶段读的,刘擎特别欣赏其中大段的说教性文字。屠格涅夫也是他喜欢的作家,但是,当他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,才觉得这是真正伟大的作品。
他的文艺天分被激发出来,参加了学校里的诗社、戏剧社,也开始尝试创作,写诗、写戏剧、写文艺评论、写小说。他最喜欢和擅长的是演讲,手捧一本杂志,站在舞台上深情地诉说。他从来不背稿子,现场发挥是他的强项,因为写过戏剧的缘故,他总能找到更有力量的语言,成为上海演讲协会的“新星”。1983年10月,上海团市委组织“振兴中华演讲团”,刘擎是成员之一,去北京清华大学、人民大学演讲。回到上海的第二天,《文汇报》头版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,这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讲,几乎可以算是一夜成名。
1988年暑假,刘擎去北京参加一个讲习班。二十多天里,听周国平讲尼采、赵越胜讲马尔库塞、王炜讲海德格尔、陈宣良讲萨特、苏国勋讲韦伯、郭宏安讲加缪,还结识了《读书》杂志的沈昌文和王焱。课程结束后,他被评为优秀学员。
但是刘擎仍不确定未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。1991年,他赴美留学,先后在马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。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,是希望能回答自己的困惑:“要走现代化道路,但路上有很多挫折,怎么理解这一切?”博士有很明确的阅读要求,每周要看七八百页书,写二三十页作业,刘擎没有任何娱乐时间,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,看一天书,中午跑出来吃个三明治,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。在这个阶段,他终于确定,要以学术为自己的终身职业。